《断代》:激情过后的时代
访问量:1936
时间:2018-07-07
《断代》:激情过后的时代
文/Cor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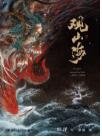
《断代》/郭强生/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是在飞机上看完《断代》的,好久没遇到这么酣畅淋漓的书,散发着一种既老派又现代、既亲切又疏远的魅力。就人物而言,代入感并不强,破落同志酒吧老板老七、事业滑坡的音乐人翁小锺 、仕途为大的政客姚瑞峰、远走国外的巨富之子阿崇、超商收银员阿龙,他们都是男性,也都曾于不同场合、时代在男同志交友圈里兜兜转转。书中还夹带了不少私货,郭强生借他人身份探讨男男之爱,对其中的爱与性表达自身思考,但就是这样一本充满了雄性荷尔蒙的书,带给我强烈得无法抵挡的 nostalgia ,尝试感知男性情欲与男男情感,同时脑中不断回放书影里的昨日台北和记忆里的今日台北。
《断代》时空承接白先勇《孽子》中的时代背景,故事从八〇年代初讲起。谈及历史背景,回溯到七十年代 PRC 入联,中华民国逐渐退出主权国家的国际组织(或改名),PRC 一步步取代其成为国际社会上“中国”的唯一代表,这对台湾造成的冲击极大,迫使当政者调整对台湾的定位,普通民众心理也有了巨大变化。与海峡对岸接连取得的外交成就相对的,是国民党及其统治下的台湾感受到的被遗弃感。当权者也不得不相应进行相应的策略调整,从反攻大陆的宣传中抽身而退,不再继续与大陆争夺正统性议题,转而将目光投向被压抑数十载的乡土甚至日据时代的文化,来强化“台湾主体意识”的概念。这种国族认同变化体现在民众身上,便不再是口号,而是在时代浪潮中人们如何继续着自己柴米油盐。这一社会变动与书中描绘的同志生活有什么联系呢?换句话说,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同志的境遇是怎样的?
台湾似乎又陷入了亚细亚孤儿的处境,不再是中日拉锯战的“弃儿”,而是在中美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博弈中的“交易品”。尚未能在国际秩序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也从未被孤独地隔离在世界之外,西洋流行乐纷至沓来,拨动着年轻人躁动不安的心弦,不断融合吸取外来文化,即便无人知晓何处是归乡。美乐地的男同志们虽不知道,几年前大海对岸哈维米尔克的抗争,共鸣了多少挣扎的人心,鼓舞了多少同志勇敢站出来、做真实的自己、追求平等权利的决心与意志,但他们目睹了丰富多彩的次文化的萌芽,在以本土文化为主体、外来文化大量涌入的八十年代初,同志酒吧开始出现在台北的大街小巷里,交友方式再简单不过,夜深人静之时潜入美乐地,点杯小酒,看到钟意的男子,跟酒保(通常就是老七)示意,帮忙点个酒,传个小纸条,跟考试作弊还有几分相似。然而,即便想对自己坦白,也不知从何谈起,能仰仗的领路人寥寥无几:没有活跃于公共视野内的同志偶像,没有真正宽容的土壤,不存在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
华灯初上,出入美乐地的人形形色色,虽不乏汤哥这种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但大多数人还是深柜,深夜寻欢作乐,天一亮就重新披上伪装。虚假的生活如同硬壳,保护着有血有肉且真实的自我。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走入家庭,有些人徘徊在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往来众人,读者对姚瑞峰的态度或最为矛盾,他涉足了书中所有人的生活,他是小锺弹吉他时脑海里浮现出的身影,是阿崇那年夏日无疾而终的痴恋,是老七口中高大俊朗的名校生。然而,在他心中仕途的重要性无可比拟,他被男性的肉体所吸引、被同性情欲搅得心乱如麻,但这一切都抵不过立委头衔,他结了婚,还有了孩子,成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却永远地失去了成为一个合格恋人的资格。高档餐厅里,望着被电话搅得心神不宁的姚瑞峰,不知该开心还是伤心。
如今,泛滥的交友软件几乎取代了不见天日的同志据点,无需冒着被识破的风险、冒着遇到熟人的尴尬、冒着夜行的恐惧。美乐地这样的地方终究只会变为尘埃,尘封历史之中,没人愿意踏足,生怕溅得自己一身泥。从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中走过,如若侥幸捡得一条命,到了风烛残年,容颜日渐老去、躯体日渐衰弱,再加上“孤独”二字,在这种状态中度日,岂不是比死亡更悲惨的命运?同志该如何养老、如何老有所终?没有婚姻制度的保障,承诺像一个吹得很大的气泡,一触即破,有时甚至不攻自破。
年纪尚小,不去想当引以为傲的身体资本不复存在时,糟心的事会不会持续发酵,推倒了内心的多米诺骨牌防线,面对一连串的心态失衡,任何止损的招数都无济于事,只得接受命运的残酷安排。毕竟,“这个世界到今天只走到了青春健美的男孩们高呼同志无罪,没有人可以告诉他们接下来该怎样面对老与丑、病与残。“ 老七抱怨,“难道七老八十了,还要他们跟院里其他的老太婆们搞联谊不成?” 终生未婚,膝下无子,身旁无伴,更凄凉的是,一起走过风华正茂年岁的“姐妹们”,多数成了枯骨野鬼。因为走过那个年代的男同志,不可避免地经历过一场惨烈的战争——艾滋病肆虐。
小锺活着熬过了最糟糕的时候,却无法面对生的煎熬。爱滋带原者的标签如影随形,犹如一个甩不掉的影子,阳光越是强烈,影子越是凶猛,使得他在已经狭隘的族群里依旧备受排挤。即便偶尔有人依然倾心于这个风光不再的中年人,听闻那场席卷人命的疾病留给他的“罪证”,往往无疾而终。厌世者的标签却不是自己贴上的,他始终忘不了高中时的那一幕,他以为的爱情,葬送于彼此的小心翼翼和畏畏缩缩中,自那以后,所有的寻寻觅觅似乎都欠缺了什么,达不到完满。“幸福是一种决心”,可惜这是一个过时的信仰。微小个体对时代似乎无足轻重,只能说,那些努力活出最真实、最完整的自我的个体给时代添加了鲜亮的一抹色彩。
虽然是烂命一条,至少知道生错的是时代,不是自己。
无论人或物,无论生或死,无论喜或悲,全都变成了回忆。没什么好追忆的,体内流着艾滋血液的生灵,像杂草一样在岁月里无声燃烧。那团团烈焰,照亮了新世代的征程。
郭强生接受采访时提到,“故事中,一定要存在属于这个时代的人,不能只是沉溺在八〇年代。看望过去的理由,是为了看接下来要如何走。”他在故事里安插了阿龙这一位双性恋人物。从阿龙的视角切入,剖析当代年轻人面临的挣扎与矛盾。阿龙是书里唯一的年轻人,一出场时自我认同还是异性恋,但他的爱情也不符合世俗期待。他迷恋着那个记忆中的少女偶像,即使她已坠入风尘。不知是爱上同性还是爱上陪酒女在他人看来更为离经叛道,或者说,反叛行为无需一较高下,说好听点,叫不惧世俗眼光、敢于追求真爱,说难听点,叫“反常”,虽然“常”的定义无从追究。
阿龙曾以为自己是个百分百的异性恋。在意外得知曾向他表露过情意的 Tony 自杀的消息后,阿龙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适逢美乐地发生一件件奇闻怪事,他踏上了重新发现自我、发现爱情的道路。
遇鬼或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阿龙深夜路过美乐地,竟能看到男同志的游魂,只有在美乐地这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小角落里,他们才能活出真实的自我,因此死后依旧不忍离去,继续着生前的聚会与派对。我尝试从两个方面来解读鬼这一意象,一指死后灵魂找不到归宿的同志,《寻梦环游记》热映之际,有人评论道,影片的世界设定是同志无后群体的噩梦,如果死后没有后代记得、没有定期祭拜,魂魄状态会每况愈下,直至彻底消亡。没有按照世俗的期待成家的男人,成了不断游荡的孤魂野鬼。老七常常回想起酒吧最热闹繁华的年代,和许许多多熟悉的面孔,可在世的朋友却寥寥无几了,知心故交先他一步去了阴间,等着他来汇合,继续当他们的店长。无后的他们很快就会被人遗忘,只想在烟消云散之前,求得无数个彻夜的痛饮狂欢。
从现实意义上说,鬼和那个年代的同志有许多共同特征:“鬼和同志一样,都是既怕被看见,又希望被看见的一群”。Penguin 写的,“在同志权利暗哑无声的时代,同志只能在黑暗处出没,借此藏身,完成欲望的宣泄。无论是白先勇笔下的公园,还是郭强生笔下的同志夜店,都是黑夜的产物。一旦白昼来临,众人就隐身到各自的角落。” 这与游鬼的处境何曾相似。在1996年底台北市女权火照夜路大游行(这一活动同样有同志群体参与)中,大家喊出了“妇女要夜行权,同志要日行权”的口号,这是同志游行的前哨站。历经二十多载的斗争,台湾于去年中通过了同性恋婚姻法案,成为亚洲之首,往平权的方向迈进一大步,法律权益和社会态度的积极巨变似乎昭示了光明的前景,但不能忘却的是——新生代享受着的是他人受难的成果,始终是从别人的牺牲中获益。
从老一辈的手中接过抗争的火炬,然而,看得见的是同志骄傲大游行上的狂野欢快、自由不羁,看不见的是前辈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遭受的苦难。这其中的世代隔阂让人唏嘘动情,老七慨叹新生代的同志只图自己开心,游行不过是场嘉年华,若推门进来看到这些孤疾老怪者,连表面的礼貌也不顾及撒腿就跑。谁会记得他们曾经遭受的各种歧视和侮辱?又有谁会替他们经历过不公平待遇发生?惨痛的过去也只有沦为尘埃的命运,被埋没在历史的沙堆里。虽然新生代能做的远多过于身着张扬个性的服饰、站在远处遥望着时代落幕。
书后附上了何敬尧专访郭强生的文字记录,其中郭提到“纯真失落、激情过后”,这是从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提纯的概念:虽然威权体制瓦解了,台湾举办了民主形式的选举、公民被赋予投票的权利,但民主与自由的斗争取得胜利、新体制尚未健全之际,该怎么应对这种胜利后的迷惘、空虚与怅然若失?该如何走好个体的人生之路与社会的发展之路?不再是被动沉默者,必须自己做出选择,同时为此负责。这和台湾同志平权运动面临的局面有类似之处,面对护家盟等恐同团体的挑衅,有着共同的敌人,诉求不一的同志团体同仇敌忾,更能凝聚起来、团结一心,但若是在斗争中暂时取得了胜利,这种 comradeship 还能持续多久?如何分配胜利成果?如何保证大家还能像斗争时那样同心协力?该如何继续这场战役?其实,连是否需要继续斗争都是个无解的问题。
痴嗔怨念甚至艾滋病毒都不致命,“激情过后”的无所适从才是痛苦源。郭强生在部分章节,用王尔德、萨特、加缪等的名句作为引言,“我想探索一个新时代的存在主义需要思考的问题。我想要回到存在主义式的疑问:关于同志的‘存在’是什么?” 当下,社会家庭制度面临诸多挑战,不仅是同志婚姻合法化对传统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冲击(有观点认为,同志追求法律上的婚姻平权实质上是对传统观念中婚姻家庭制度的妥协),更有开放的性观念、多种家庭组合方式对社会结构造成的潜在颠覆,“以往相信的性、婚姻、家庭三者合一的关系也可能面临崩解”,在这种局面下,“我究竟是谁?”该如何在社会中寻找我的位置,如果传统家庭结构已处于巨变边缘?
当社会变得越来越包容和多元化的时候,同性恋不再是完全见不得光的事,也有越来越多的公益团体和组织致力于帮助处在困惑期的性少数重构自我认同。然而,继“我是谁?”后,紧接而来的课题是我该如何去爱。现代人该如何相爱?这个问题是不分同性或异性恋的。什么是纯粹的爱情?爱情的本质是什么?应该如何爱一个人?正如王德威所指出的,”对郭强生而言,推理的底线不是谁是同志与否,而是爱情的真相。”这让我想到曾经看过的书里提及的采访,记者问意大利同志导演维斯康蒂是否觉得自己欠缺什么,他说:“那种发自内心想要寻求的爱情,(却)无处可寻。”
对普世价值的讨论浅尝即止,回归《断代》的地域性。去年四月,纪大伟教授造访伯克利时,有幸见面,适逢台湾同婚释宪结果出炉,大家就此事谈论不休。纪说,台湾同运确实取得了一大胜利,但许多难题仍未解决,因为我们还处在模仿西方模式的阶段,迫在眉睫的或是思考如何将东方传统文化融合到同运中,寻找更有效、更得人心的斗争方式。一些人认为同性恋是西方舶来品,是被西方文明腐蚀的结果,但稍加了解,就知道同性恋在中国有悠久历史,古籍中都有记载。而当下,我们对同性恋的认知、解读,甚至斗争的理论依据和行为方式,深受西方影响。
然而,在中华文化语境下,非异性恋者所需要考虑的事情与西方同志运动先行者不尽相同,传统思想观念中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孝道潜移默化对子女进行道德捆绑,公然干涉同志社群的人生抉择。在这里引 Rema 在书评中写的一句话,“当我们把这样的同性欲望放到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它需要面临的是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在我们身上埋下的种子。它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同性欲望,而是受到强烈的道德观念和社会人情的影响。”这是西方平权运动中的空白页,却是东方背景下同运不可或缺的关键词。如何在受到西方同志权利运动的影响下,建立更有效的本土斗争模式,为 LGBTQA+ 社群发声,或是”激情过后“我们需要用心思考的话题。
__本文转载自豆瓣书评

















